Science:大有可为的抗癌新疗法
| 导读 |
尽管Carl June这一生非常曲折,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行进在开发抗癌新疗法的科研道路上。
Carl June等人正在开发一种T细胞抗癌疗法,不过这条路可不容易,充满了起伏和变数,能否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
2011年1月的一个下午,肿瘤学家Carl June和David Porter在Perelman先进医学中心(Perelm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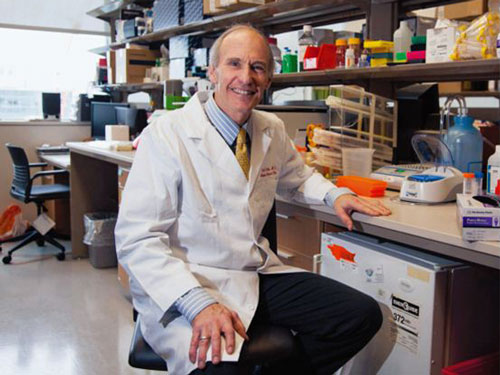
尽管Carl June这一生非常曲折,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行进在开发抗癌新疗法的科研道路上。
Carl June等人正在开发一种T细胞抗癌疗法,不过这条路可不容易,充满了起伏和变数,能否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
2011年1月的一个下午,肿瘤学家Carl June和David Porter在Perelman先进医学中心(Perelman Center for Advanced Medicine)中庭一家名为Gia Pronto的咖啡馆里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Perelman先进医学中心就坐落在美国费城西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城(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massive medical complex in West Philadelphia)的中央地带,是一栋钢结构的玻璃幕墙大楼,离斯库基尔河(Schuylkill River,该河从费城中间穿过,将费城一分为二)只有几个街区。从Gia Pronto咖啡馆望出去可以看到林立的起重机,费城也正在大搞城市建设。
June和Porter当时碰上了一点麻烦。他们在2010年的夏天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6个星期,因为他们治好了3名白血病患者,这3名患者在此之前已经被宣判无药可治了。June和Porter当时开展的是一种新型的细胞疗法(cell therapy)试验,他们提取了患者自身的T细胞,然后在实验室里对细胞进行遗传学改造(genetically engineered),再将改造过的细胞回输到患者体内,让细胞在人体内增殖,找到肿瘤细胞,并且杀灭肿瘤细胞。这次细胞疗法试验的结果让所有医生都没有想到,每一名患者体内至少都有好几磅的肿瘤细胞被消灭了。其中有一名患者是一位64岁的老头,他名叫Douglas Olson,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科研人员,他的T细胞在实验室体外培养环境下长得并不是太好,所以他只接受了进行小鼠试验时给试验小鼠注射的细胞剂量,但是接受治疗之后的效果却出奇的好,这位患者现在每天都可以跑步了,而且还在教他的孙子如何驾驶帆船。
为这3名患者准备T细胞一共花费了35万美元。这一下子就让June和Porter“破产”了,而且他们用来改造T细胞的载体——灭活的HIV病毒也用光了。于是他们向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等机构发出了“求救信”,向他们介绍了这3名白血病患者的治疗成果(当时这些数据还没有发表),希望能够筹集到更多的经费继续开展他们的临床试验。在这次临床实验中,Olson和一位患者体内的肿瘤细胞已经全部被杀死了,另外一位患者最开始也取得了不错的疗效,可后来还是因为白血病不幸去世了。然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等单位都认为这种细胞抗癌疗法还只是处于试验研究阶段,至少在当时还不太适于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所以June和Porter碰了一圈钉子。
“当时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好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时候。” June这样说道,他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科研小团队,Porter也是他们课题组的成员之一。虽然June等人并不是第一个开展这种细胞疗法人体试验的人,但是他们的实验结果却是最好的。June接着说道:“我们意识到这种细胞疗法一定有一些治疗效果,哪怕这疗效只是昙花一现,都不能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也相信这种细胞疗法一定有效,我们绝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我们意识到这种细胞疗法一定有一些治疗效果,我们绝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ABRAMSON癌症中心,CARL JUNE Porter和June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他们非常想召集更多的白血病患者进行细胞抗癌疗法的临床试验,可是他们却还是没能筹集到足够的科研经费。“我们甚至想过先把这3名患者的试验结果总结一下发表算了。” June这样说道。他们希望这么做能够让事情出现一点转机。Porter也同意试一试,不过他们实在想不出哪一份还不错的杂志会接受他们这篇只有3名患者的试验数据的论文。
可最后的结果却大大地出乎了他们的预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接受了他们的报道文章。这篇文章只介绍了Olson的治疗经过,当然也重点提到了Olson只接受了小鼠治疗剂量的抗癌细胞。《科学》(Science)杂志的子刊——《科学 转化医学》(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杂志也接受了介绍所有这3名患者治疗情况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同时在2011年的8月10日得以发表。同一天,June等人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在学校网站的主页上刊登了相关的新闻,新闻的题目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研人员报道,经过人工遗传改造的T细胞连环杀手能够杀死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体内的肿瘤细胞(Genetically Modified Serial Killer T Cells Obliterate Tumor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Penn Researchers Report)”。
当这些好消息传来的时候,Porter正和他的家人去美国马里兰州的西部地区度假,他回忆说:“我那天在车上坐了8个小时,结果这8个小时我就没闲着,不停的接电话、回邮件。这个消息对我们课题组的所有人都是一个大惊喜,而且这消息迅速就传开了。”很快,June就收到了5000多份治疗申请,全世界也有800多个媒体报道了他们的科研成果。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也重新审核了June的申请,给他们课题组提供了4年共计200万美元(每年50万美元)的资助。制药公司们也开始主动找上门来了。就在他们的文章发表之后快一年的时候,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签订了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协议,为June等人提供帮助,让他们开发的这种抗癌新疗法能够通过药物监管部门的审批。Olson和另外一位患者到现在病情都还非常的稳定,他们俩就是June一直期望出现的“幸运星”。
现在,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成千上万的肿瘤患者都在期盼T细胞疗法快点到来,可是目前看起来这似乎还是遥遥无期的。这是因为这种疗法还只是对一部分的血癌患者有效,而且依旧还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收治了30多名患者,在其他地方也有50多名患者接受了这种T细胞治疗,可不是每位患者都能够出现奇迹,而且还有一些患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就算是治疗效果很好的患者,也没人知道他们的病情在什么时候会复发。据Porter介绍,医学文献中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例子,证实那些药物对受试的病人——也许只有10个——有效,而事实上,这些药物却并未取得成功。
医学文献中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例子,证实那些药物对受试的病人——也许只有10个——有效果,而事实上,这些药物却并未取得成功。——宾夕法尼亚大学ABRAMSON肿瘤研究中心DAVID PORTER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时刻保持谨慎,但事实上却很难如此冷静而不被打动。虽然病例数还非常少,但是很多肿瘤学专家都相信June等人正在开展的细胞疗法试验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作。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次抗癌细胞试验成功过。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人工T细胞疗法再往前走一步,如何在更多的医疗机构里、对更多的患者、对患有其他不同癌症的患者进行临床试验。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的肿瘤外科专家Steven Rosenberg数十年来一直都在研究细胞抗癌疗法,他介绍说:“制药公司可不在乎在前期投入5亿美元,他们只要你最后能够只花1美元制造出产品就行。”正如Rosenberg介绍的那样,这就是目前T细胞疗法面临的问题,因为现在每一个批次的细胞产品都不一样,而且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可能因为人工操作出现问题。
由于这一次是科研人员和制药公司共同开发一款新型的抗癌药物,所以June等人的课题组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大家给予赞美的同时,也会时不时地传出一些批评的声音,有人认为June等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甚至还有人起诉June等人,说他们违背了合作协议。不过他们也的确是急于挽救患者的生命,比如“肿瘤”在June自己的自传里就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例。但是无可否认,这也的确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和荣誉,同时也是第一次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来消灭肿瘤。
重建患者自身的T细胞
June工作的主要思路其实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以色列免疫学家Zelig Eshhar的突发奇想。Eshhar当时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罗奥图(Palo Alto, California)度假,不过那时他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让免疫系统的卫兵——T细胞攻击其它目标呢?Eshhar知道这首先就得让T细胞能够识别、并且锁定那些平时不能够识别的靶标分子。在T细胞上插入一段外源的DNA,改变T细胞表达的受体就是唯一的办法。
Eshhar渡假结束回到位于以色列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in Rehovot, Israel)之后就立即开始了这项工作。可惜当时的遗传工程学技术还不够发达,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Eshhar终于成功了,他将一段基因序列插入了一种永生化的T细胞(因为这种细胞更容易接纳外源的DNA)内,成功地让T细胞有了新的“敌人”。Eshhar回忆说:“在我们成功之后,我不想说我们彻底被这种技术迷住了,但是我们的确是被它吸引了。”
可是Eshhar的成功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如果要治疗癌症这样的疾病,我们首先就需要找到肿瘤细胞特有的靶标蛋白质分子,否则人工改造过的T细胞就无法区分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有可能会误伤正常的人体组织。我们还必须确保这种人工T细胞在回输到人体内之后也能够正常地分裂、增殖,能够长期在人体内存活,这样才能保证彻底地消灭肿瘤组织,并且能够确保肿瘤不会复发。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且接受了Eshhar的理论,并且也加入了进来,推动这项技术继续向前发展。在美国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纪念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in New York City)里,肿瘤科医生,同时也是细胞治疗专家的Michel Sadelain也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我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来改进这项技术,希望提高外源基因转染的效率,至少能够让0.5%的人工培养细胞能够被成功地转染。现在,我们随便找一个高中生来都可以教会他们完成这一系列的操作。”Sadelain介绍说。Sadelain自己给这种人工T细胞起了个名字,叫做“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细胞,或者简称CAR细胞。
Sadelain从一开始就选定了肿瘤作为自己的攻关目标,但June可不是这样,他是兜了一番圈子之后才进入这一行的。June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上世纪的冷战时期,准确的说是源于越战时期。1971年时他刚满18岁,当时碰巧有一个机会可以参军入伍(免费接受教育),所以他放弃了申请去斯坦福大学上大学的念头,应征加入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 in Annapolis, Maryland)。可是越战在两年之后就结束了,不过June还是选择继续呆在部队里,完成了他的医学课程。由于当时美国担心可能爆发核战争,所以June接受的教育主要都是与肿瘤和骨髓移植技术(可用于治疗因遭受高剂量核辐射而患上的白血病等疾病)相关的内容。到了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彻底结束。“部队再也不需要骨髓移植医生了。所以我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June介绍说。
美国海军并不打算对肿瘤研究提供科研资助,所以当时还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海军医学研究所(Nav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Bethesda)工作的June选择以HIV作为新的研究方向。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决定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就是通过对HIV的研究才让June对T细胞和人体免疫系统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他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June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如何让艾滋病患者体内的T细胞多起来(我们知道HIV病毒破坏的就是人体内的T细胞)。当时June实验室的免疫学家Bruce Levine正在研究促进T细胞生长的方法,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T细胞,让这些细胞在体外试验中消灭自己的靶标。
1995年,因为一次意外,June的私人生活和科研生涯“被迫”走到了一起。因为他的妻子Cynthia被诊断出患上了卵巢癌(ovarian cancer)。当时他们的小女儿刚3岁,另外两个儿子也才十几岁。“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患者家属的心情。” June回忆说。当时June坚信通过对人体免疫系统进行调控是可以治疗肿瘤的,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一种成熟的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可供他们采用。
Cynthia June在2001年因病去世,时年46岁。当时June刚刚离开美国海军,全家搬到费城不久,他们的小女儿也已经9岁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也多亏了大家的帮助。” June还沉浸在那段往事当中,慢慢地回忆道。
Cynthia的去世也给June的身边的人带来了影响。Levine就说道:“我们都认识Cindy,也和她很熟。我们目睹了她从生病到去世的整个过程,也看到了这一切对Carl的打击。这种事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同时对我们的整个研究工作也带来了影响。”
成功与失败
搬到费城之后,June还是在继续他的HIV研究工作,但因为他妻子的事情,以及对用CAR细胞一定能够成功治愈患者的信念,他也开始开展了一些肿瘤方面的研究工作。June的工作也得到了另外两位肿瘤学家的热烈支持,他们俩分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Abramson癌症中心(Penn’s Abramson Cancer Center)的白血病医生Porter,和美国费城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CHOP)的Stephan Grupp。有一天,Grupp甚至主动来到June的办公室寻求合作。

审慎的乐观主义者。肿瘤学家David Porter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加入他们的临床实验,随着这些患者的治愈,也能够让他们的T细胞疗法得到更进一步的验证。
除了June之外,还有很多科研人员也都在尝试用CAR细胞治疗癌症患者,其中就包括美国斯隆-凯特林纪念癌症中心的Sadelain、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的Rosenberg,和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in Houston, Texas)的Malcolm Brenner等人。他们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癌症靶标——CD19分子。只有B细胞能够表达CD19分子,在患上了B细胞白血病(B cell leukemias)之后,患者体内的B细胞会大量增殖。之所以选择CD19分子主要是因为以下这两点考虑,首先,CD19分子是一个著名的靶标,该分子在所有癌变的B细胞上都有表达。另外,虽然B细胞也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于我们人体的生存而言却并不是必需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攻击CD19分子时必然会杀伤正常的B细胞。
但是如何设计出特异性针对CD19分子的CAR细胞却是一个大难题。Sadelain介绍说:“有各种各样的CAR细胞。”我们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方法,设计出能够与CD19分子结合的受体。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分子就是“共刺激信号(co-stimulatory signal)受体”,CAR细胞表达这种受体,可以促使CAR细胞活化,并且让CAR细胞能够在患者体内长期存活。Sadelain的科研团队也和其他的课题组一样,用小鼠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最终锁定了CD28这个分子。Rosenberg和另外两个课题组也分别选定了CD28分子。所有这4个课题组后来也都开展了相应的临床试验工作,甚至连时间都和June实验的开始时间相差无几。
不过June却选择了另外一个靶标——4-1BB,这也是一种共刺激受体。June之所以选择这个分子作为靶标,一方面是为了体现他自己的工作成绩,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实验室发现,4-1BB分子能够帮助T细胞增殖。在小鼠实验中发现,4-1BB分子表现很不错,但还是不如CD28分子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in Memphis, Tennessee)的肿瘤学家Dario Campana领导的科研小组利用4-1BB分子第一个设计出了CAR细胞。和其他的课题组不同,June选择使用失活的HIV病毒来构建人工T细胞,他们实验室培养T细胞的方法也和其他人有所区别。
随着CAR细胞的不断出现,相关的抗癌研究也慢慢地多了起来。最先发表的就是Rosenberg课题组构建的抗CD19分子的CAR细胞,这篇文章于2010年发表。Rosenberg他们采用的是CD28分子,结果有一名淋巴瘤(lymphoma)患者接受治疗之后,病情得到了长期的部分缓解。但最终还是June等人在费城利用4-1BB CAR细胞针对那3例白血病患者开展的临床试验取得了巨大的反响,轰动了整个肿瘤研究领域,也让公众认识了这种新疗法。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杜瓦迪市城市希望医院(City of Hope in Duarte, California)里从事血癌治疗工作的Ravi Bhatia这样评价道:“这些成功的案例至少让我这样的怀疑论者有了信心。” Bhatia的医院也一直在研究CAR疗法,但是他们将T细胞移植入患者的体内之后,这些细胞很快就消失了。所以Bhatia说:“如何让细胞持续存在下去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June、Porter、Levine和Grupp(他正准备第一次用CAR细胞为一名患儿进行治疗)四人都准备在这个方向上大干一场。“你们经过前期的努力后,仍然应该努力保持脚踏实地的态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Levine这样说道。这场科研竞赛非常激烈,而且有些时候也不那么友好。Rosenberg和June曾经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就Rosenberg的CAR疗法是否成功这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Rosenberg曾经在June的文章刊登之前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了他们用CAR疗法取得的抗癌治疗效果,但是June认为当时不是因为人工T细胞发挥了作用,而是患者在之前接受的化疗为后来的T细胞奠定了基础。“那简直就是一次针尖对麦芒式的争论。” Sadelain回忆说。
你们经过前期的努力后,仍然应该努力保持脚踏实地的态度,清醒的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宾夕法尼亚大学BRUCE LEVINE
但是最大的一场争论还得算是2012年的7月发生的那次事件。当时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向法院起诉宾夕法尼亚大学,指控宾夕法尼亚大学违背了和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在2003年签署的科研材料转移协议(materials transfer agreements),因为Campana在2007年擅自向June提供了CAR细胞材料。
宾夕法尼亚大学也迅速做出了回应,指出June的CAR细胞和Campana的并不一样。起诉还不到3周,也就是在2012年的8月,诺华制药公司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公布了一份共同开发商业化T细胞疗法的合作协议书。诺华制药公司表示,他们将提供2000万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内新建一座细胞治疗研究中心。
这场官司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也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到了2013年的3月,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为Campana的4-1BB受体结构域T细胞申请的专利终于获批。
3天之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向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决Campana的专利无效。这场官司表明,对于谁拥有哪些科研成果,大家都各执一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律师表示他们只是需要获得一个公正的判决,并不想染指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专利。
不过不论是June还是目前已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工作的Campana,谁都不愿意对此事发表评论。诺华制药公司的发言人Scott Young也没有介绍太多的情况,他只是表示,诺华制药公司并没有牵扯到这3起官司当中,不过Young在电子邮件里也强调到:“我们对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合作充满了信心。”
克服困难
目前诺华制药公司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合作进展的非常顺利。在诺华制药公司方面,已经有好几十人开始研究如何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的T细胞治疗。诺华制药公司需要先确定这些人工T细胞在人体外能够存活多久,然后才能够决定需要购买多少台细胞处理设备。他们决定尽可能地使用机器来处理、培养这些T细胞,尽可能地实现自动化操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可以减少因为人工操作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他们也在研究在体外对细胞进行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即从人体内取出细胞至回输这些细胞之间的时间,诺华制药公司希望这个时间能够越短越好,目前暂定的是3个礼拜。
“所有这些细节因素都需要提前考虑好,不仅仅在美国是这样,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 诺华制药公司肿瘤药物部门负责监管这整个T细胞工作的Manuel Litchman这样说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里,Levine正在紧张地培训诺华制药公司的员工。诺华制药公司的管理层每周都会和June的课题组碰好几次面。在去年的12月,诺华制药公司还花费了43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新泽西州的莫里斯普莱恩斯(Morris Plains, New Jersey)的一个免疫治疗药物制造工厂,这家工厂之前是Dendreon公司所有,主要用于生产前列腺癌疫苗产品的。Litchman介绍说:“我们可不想这间位于莫里斯普莱恩斯的工厂和Bruce的实验室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是要在莫里斯普莱恩斯复制大量的Bruce实验室。”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细胞产品的一致性问题。由于这些细胞都采自不同的患者,所以每一个批次的T细胞产品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其他的科学方面的因素(比如用于插入外源基因的载体),以及生产方面的因素(比如运输的方式),也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June等人在这方面就有过惨痛的教训。他们在前三名患者的实验中取得成功之后,又在2012年的1月对另外3名患者进行了治疗(不过这一次使用了另外一种载体),可是这一次治疗没有产生任何疗效。“我当时郁闷到了极点。” June回忆说。他完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至今都还不知道是载体出了问题,还是正常的疗效波动现象。“我们就知道这种细胞疗法之前成功了3次,现在又失败了3次。后来这3名患者都因病去世了。” June继续说道。
接下来他们又选择了第7名患者进行治疗,她就是当时年仅6岁的白血病晚期患儿Emily Whitehead。Whitehead的父母来找June时都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可这一次的结果又让人们大吃了一惊。June等人的治疗措施让Whitehead的体内发生了超强的免疫反应,结果Whitehead在费城儿童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躺了两个星期,医生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挽救她的生命。
“本来我们认为Whitehead应该是挺不过来的。” June介绍说。他甚至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督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里这样写到:“我很遗憾地告诉您,我们CART19试验中的第一位儿童患者可能活不下来了。我们现在已经束手无策,只能祈祷奇迹能够发生。我希望能够启动调查程序。”可最后的结果却出乎大家的预料,所以June的这封邮件也没有发出去。
就在医生们聚精会神的分析小Emily的检查结果时他们发现,Emily体内大量的T细胞分泌了超量的白介素6(interleukin-6),原来这才是令Emily限于危险境地的原因。于是医生们赶紧给她用了一种用于治疗关节炎(arthritis)的药物,这是一种白介素6抑制剂,最后小Emily获救了,她也成了整个医院的经典病例。June能够想到用这款药物也是出于偶然,因为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不久,他的女儿Sarah就被诊断出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所以她一直在服用这种药物。Grupp也发现了同样的抗白介素6药物,因为有一次他的同事用他的苹果手机谷歌了一下这个药,后来被他无意间看到了。
现在,Emily的病情已经缓解了1年多了,她的头发也长出来了,都可以扎马尾辫了,而且马上就要过8岁生日了。Grupp发现Emily有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所以她非常容易出现超敏反应,这也解释了她当初为什么接受T细胞治疗之后的反应会那么大。从那以后,Grupp在给其他小朋友进行治疗时使用的细胞剂量就只有当初Emily接受的治疗剂量的十分之一,虽然他自己内心中也不能确定用“药”剂量的影响作用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因为细胞进入人体之后虽然也会增殖,但同时也会死亡。在Emily之后,所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展的临床试验都会借鉴她的经验和教训。Levine甚至还在他的办公室里挂上了Emily的照片。目前已经再婚,并且又有了一个10岁大的女儿的June在说起Emily,以及Emily的家庭时都会禁不住哽咽起来。

幸存者。8岁的Emily Whitehead是第一位接受CAR细胞治疗的儿童患者,不过她经过治疗之后已经生存了1年以上。
对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而言,Emily和其他的那些患者都是活生生的教材,“教会”了我们人工T细胞都会起到哪些作用。Grupp说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除了接受媒体的关注,和大量的、来自患者及其家庭的咨询之外,Grupp也会在facebook上接受之前治疗过的患儿的家长给他发来的有关患儿身体状况的最新消息,然后Grupp才会将这些最新的信息通报给同行。“不过我现在几乎已经不能保守什么秘密了,这些最新的结果往往还没有得到同行的评议就已经‘泄漏’出去了。这一点完全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在这方面做的准备工作也最少。这也是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一点。” Grupp介绍道。
到目前为止,Grupp已经治疗了14名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的患儿。其中有5人的治疗结果被他写成了论文并公开发表,或者在学术大会上做报告介绍过。在这5个人当中,有4人的病情得到了缓解,另外1人后来又复发了。Porter也在今年5月召开的一次科学大会上汇报了他们对成年人患者进行治疗的成果,他们一共对17名成人患者进行了治疗,其中有10人对治疗有反应,5人达到了病情完全缓解至少3个月以上的疗效。
Porter等人发现,基本上每注入一个T细胞,就会杀死1000至9.3万个白血病肿瘤细胞,这说明这些T细胞在注入人体内之后进行了增殖和扩增。Porter小组正在对这种细胞增殖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们初步怀疑可能是Campana最开始使用的4-1BB分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最开始预计的一样,患者在经过治疗之后,他们体内正常的B细胞也被杀死了,不过这会对患者带来怎样的长远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需要进一步观察。值得一提的是,CAR疗法的费用有了大幅度的降低,不过目前还是需要2万至4万美元,这还只是构建T细胞的费用,不包括细胞注射之后的支持治疗的费用。
今年3月,Sadelain在《科学 转化医学》(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他们对5名急性白血病患者的治疗成果。由于这种白血病要比慢性白血病更加凶险,所以肿瘤科医生们读到这篇文章之后都倍感兴奋,因为据这篇文章介绍,在接受了治疗的5名患者当中,有4人都达到了临床缓解的效果,而获得临床缓解是让病人能够接受骨髓移植治疗的先决条件,所以这对于患者和医生们无疑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5名患者接受治疗至今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当中有3人目前还活着。城市希望医院的Bhatia认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另外一家机构(指的是Sadelain工作的斯隆-凯特林纪念癌症中心)也取得了同样的疗效,这一点意义重大,这说明前面取得的疗效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不过像Porter和Grupp这样的医生还是担心这种细胞疗法并不一定会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Grupp就说道:“当我在给患者做术前谈话,签署知情同意书时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些东西看一遍就够了,别往心里去。’我们不可能取得像论文里描述的那种神奇效果。”包括小Emily在内,一共也只有4个人在治疗之后活过了1年。我们也不知道CAR疗法对于治疗实体瘤(solid tumors)是否同样有效,不过June等人正在开展临床试验,证实这个问题。
当我在给患者做术前谈话,签署知情同意书时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些东西看一遍就够了,别往心里去。’我们不可能取得像论文里描述的那种神奇效果。——费城儿童医院STEPHAN GRUPP
离2010年那个辉煌的夏天已经过去了将近3年的时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研人员们还在努力的招募尽可能多的新的患者参加他们的临床试验;他们也还在和监管部门沟通,希望能够让这种细胞疗法尽早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同时也在和诺华制药公司合作,培训他们的员工,开发细胞生产流水线。“我感到累了。”Porter强调着说道。忠实的自行车骑行和跑步爱好者June也不得不放下了他的爱好,虽然他还计划在上个周末进行一次34英里的超级马拉松。June说道:“我可不习惯像现在这样每周工作这么长时间。我喜欢工作,可是我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休息。”自从诺华制药公司开始处理T细胞,制备CAR细胞之后,June就一直想找一个“接班人”。不过不论是June还是诺华制药公司都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不过对于June而言,那一天一旦到来就意味着他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在那之前,我都是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June这样说道。
原文链接:
The Dizzying Journey to a New Cancer Arsenal

来源:lifeomics
 腾讯登录
腾讯登录
还没有人评论,赶快抢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