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敏:从监管视角看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的发展
| 导读 | 从化疗时代到靶向治疗,再到免疫治疗,患者的用药选择和获益程度在变化,药监局的审评标准也随之变化。琳琅满目的新药临床试验进展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当这些PD1/L1抑制剂、IDO、CAR-T类细胞治疗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涉及适应症从黑色素瘤、白血病等逐渐扩大到胃癌、结直肠癌等十多个瘤种,作为药品上市“守门员”的药品审评中心,需要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
从化疗时代到靶向治疗,再到免疫治疗,患者的用药选择和获益程度在变化,药监局的审评标准也随之变化。琳琅满目的新药临床试验进展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当这些PD1/L1抑制剂、IDO、CAR-T类细胞治疗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涉及适应症从黑色素瘤、白血病等逐渐扩大到胃癌、结直肠癌等十多个瘤种,作为药品上市“守门员”的药品审评中心,需要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哪一类患者适合免疫治疗,是按常规的组织学分型,还是按治疗线数划分,抑或是利用生物标记物?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审评,终点指标是选择ORR、PFS、OS还是别的?临床试验方案如何更好的设计,是单臂研究还是随机对照?哪些安全性问题不能接受,哪些风险需要控制?这些在审评中需要思考的问题,反过来也是需要通过临床研究来回答的问题。
7月1日在北京由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CCFDIE)主办,药品审评中心(CDE)、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CAHON)和清华大学医学院协办的“2018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研讨会”上,来自药品审评中心(CDE)的资深审评员、化药临床一部部长杨志敏,就“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的发展:监管视角”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本文围绕这一报告梳理了几个要点,供业界争鸣。
感谢杨志敏部长对原文确认和斧正。

杨志敏
药品审评中心(CDE)
资深审评员、化药临床一部部长
考虑更广阔的空间
去年,FDA首次基于肿瘤生物标志物而不是肿瘤原始位置批准了默沙东的PD-1抗体Keytruda,这是FDA对于抗肿瘤药物的新认识。目前,FDA已批准了5个免疫治疗产品,涉及10个瘤种,有单药也有联合治疗,有一线、二线也有初治,有按生物标记物分也有按组织学分。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免疫治疗的范围可能比现有的研究要宽得多。
“事实上,每一个研究都有证据证明在这个剂量下病人的获益大于风险,这可能是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也可能是在后线治疗中与安慰剂相比,还可能是与自然病史比,从而得出一个相对稳健的结果。”杨志敏进一步表示,对于国内企业而言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基于同一个靶点时,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有相同路径的成功案例;第二是不拘泥于已有的研究,基于基础研究和临床需求可以开辟更广阔的瘤种,或根据产品自身的特点进行差异化的设计,选择不同的路径。
当然,有些新药的开发脱离不了一般的规律,如免疫治疗与肿瘤微环境有关。“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在更早期介入,比如可以使用治疗性疫苗刺激肿瘤,使之产生新抗原、变得更热,这样可以提高后续治疗的效果。”
单臂试验的可行性
在去年的肿瘤免疫治疗研讨会上,研发客梳理了杨志敏对肿瘤免疫产品单臂试验的审评考量。
杨志敏表示,符合这些考量时采用单臂研究是可以的。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用原来ORR为5%的标准作为主要指标,那么单臂的ORR值有多可靠呢?是不是ORR提高到10%就一定认为它是有效的呢?在肝癌的标准治疗里有ORR只达到5%的索拉菲尼,也有分子靶向药ORR达到12%仍然在Ⅲ期试验失败的案例。
对此,杨志敏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产品本身不好,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的瘤种里,ORR的结果并不稳健。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稳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考虑患者的获益,如评估的时间、标准以及缓解持续的时间。另外,在安全性的评估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数据能够足够暴露出至少是常见的问题。”
杨志敏也指出,当同时有20多个同类产品针对同一个适应症人群开展临床试验时,都用单臂试验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的临床研究设计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在标准治疗和其他可用的药物都治疗失败以后,再使用这个产品。另一种就需要和其他的疗法相比,显示出这个产品在疗效或者安全性的优势。
临床研究的代表性
我国是肝癌大国,流行病学与欧美、日本也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晚期肝癌患者70%都失去了手术的机会。据了解,目前一线治疗药物有索拉菲尼和化疗,但中位OS仅在6个月左右,这与在肺癌上所取得的治疗突破相距甚远,同时也说明肝癌患者有极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会上,杨志敏举了一个案例,这是一项使用nivolumab开展晚期肝癌的单臂研究。根据是否感染HCV、HBV,索拉菲尼初治,以及索拉菲尼治疗进展者等,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了划分,分别形成37例病人和146例病人的两个队列。结果显示,尽管14.5%的ORR并不高,但在得到缓解的病人里mDOR达到19个月,大大超过了国内现有研究所看到的6个月。同时,在拓展的受试者中几乎一半(47.6%)的受试者有至少10个月的DOR,相比之下TKI药物则缺乏DOR。
“这些数据让我们很振奋,同时也要意识到临床研究的代表性和流行病学数据的重要性。“杨志敏进一步分析:肝癌在中国的发病率很高,新发患者占全球55%;中国肝癌患者感人的原因主要是HBV感染,这与国外有所不同;国内索拉菲尼使用比例也较国外低(20%);此外,肝外疾病发病率(80%)和甲胎蛋白APF升高率(60%),都比国外高。
基于这个研究,美国FDA批准nivolumab用于接受过索拉菲尼治疗后的肝细胞癌(HCC)患者,而欧盟则做出了不批准的结论。“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基于科学的数据来审评。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到,中国的患者在与预后相关的特征上比美国差一些,实际上HBV感染的病人ORR水平并不那么好,这就提示这个样本的代表性可能有问题。随着国内相关产品进入临床,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的数据。”杨志敏说。
各种联合的考虑
从PD1/L1显示出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为单药使用的局限性后,联合治疗被视为突破这一瓶颈的关键点之一,国内企业在联合用药上的布局也紧跟国际。“对于一些特殊的、免疫反应差、单药治疗效果不好的病人,或许联合用药是值得探索的。但也有一些是疗效的改善不足以抵消其显著增加的毒性,即并非所有的联合用药都比单药好。”杨志敏说。
以肺癌为例。免疫治疗已经在这个领域全线铺开,从新辅助到辅助,再到一线、二线、三线,各个阶段都有正在开展的研究。以一线治疗的14个研究来看,有单药、免疫联合化疗、免疫联合免疫、免疫联合化疗加抗血管、免疫联合溶瘤。
“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些研究究竟为患者带来了什么?要选什么样的人群才能获得成功?”
作为代表性的两个免疫治疗新药,在默沙东的 Keytruda(pembrolizumab)和BMS的Opdivo以往的临床研究数据中可以学习和借鉴很多,尤其是在生物标记物的使用上。在杨志敏看来,Keytruda获批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其胜出Opdivo的原因在于将适应症人群划分为PD-L表达量TPS(肿瘤比例评分)大于50%的人群。在后来的042研究中,默沙东进一步将免疫治疗的人群划分为TPS大于1%的人群,结果依然胜出。
“进一步分析这两个新药的成败案例,就会发现我们可能搞错了一些信息,如PD-L1高表达与高肿瘤突变负荷(TMB)不是一个人群,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将TMB作为一个指标来划分人群?”杨志敏建议,早期尽可能收集更多的信息,从而为后期临床试验开展的选择多样性提供保证。同时,积极推动研究者寻找更多的生物标记物,与组织学结合,甚至跨组织学。
“我们主张各个生物标记物放在一起来细分人群,使我们知道哪些使用单药、哪些使用组合以及什么样的组合才是真正有益于患者。在具有一定依据和理由的基础上,再通过不同的研究设计,来回答应如何进行组合,是序贯、同步还是交替使用。”杨志敏说。
评价标准的选择
一个药物能否通过临床试验获得上市的资格,不仅与药品本身的质量有关,还与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终点指标的选择等有关。但究其根源,无外乎结合产品的特点和早期已有的数据,选择一项能够真正反映患者临床获益的指标。
ORR是否可行?当ORR较低,而DOR很长时,能否转化为较长的PFS?当没有很好的办法准确测量ORR时,能否使用12个月的OS率?当ORR、OS、PFS、OS等多个指标联合时,药监局怎么考虑?据悉,针对这些问题CDE将会在近期发布一项关于非小细胞肺癌终点选择的指导原则,详细阐述各项终点指标考虑的依据。
杨志敏直言免疫毒性等安全性和数据质量仍然是药品审评环节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创新的道路上,可能未来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但数据质量这一关是我们必须要迈过去的。只有好的质量才能得出稳健、可靠、可信的结论。”此外,她考虑的还有伴随诊断、超进展的病人,以及如何控制医生的教育、如何帮助患者渡过难关等问题。她呼吁监管部门、医生、患者、研究者、申办方等各方能够密切配合,共同为推动药物创新出力。
在肿瘤免疫治疗这一前沿领域,国内审评标准的逐步建立,也是CDE自身能力不断提升的一个印证。尽管对于同一份临床试验数据,各个国家的监管部门会根据各自的医疗实践给出不同的结论,但基于科学的审评是每一个监管机构的立场和原则。随着国际多中心临床在中国的开展和国内创新企业的实践,中国的药监部门将越来越有能力基于中国的数据做出科学的评价和独立的决策。(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腾讯登录
腾讯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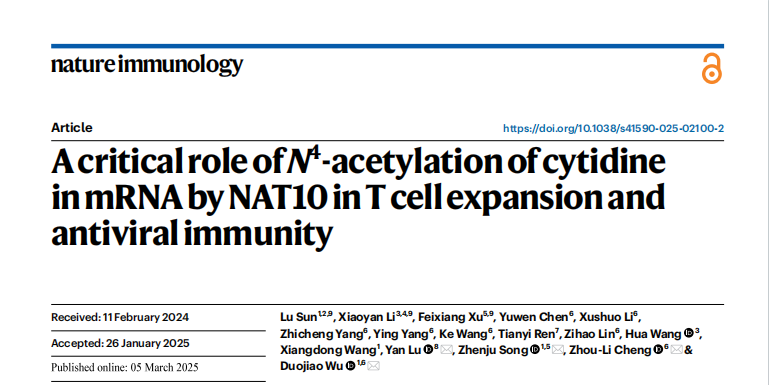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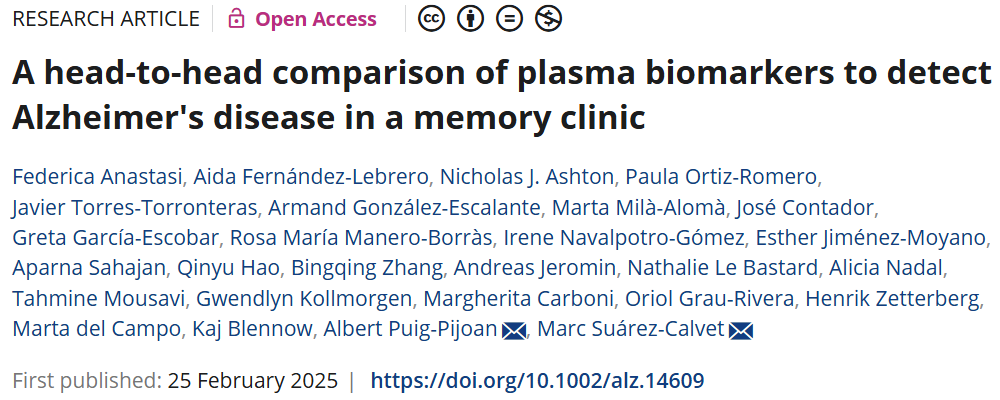



还没有人评论,赶快抢个沙发